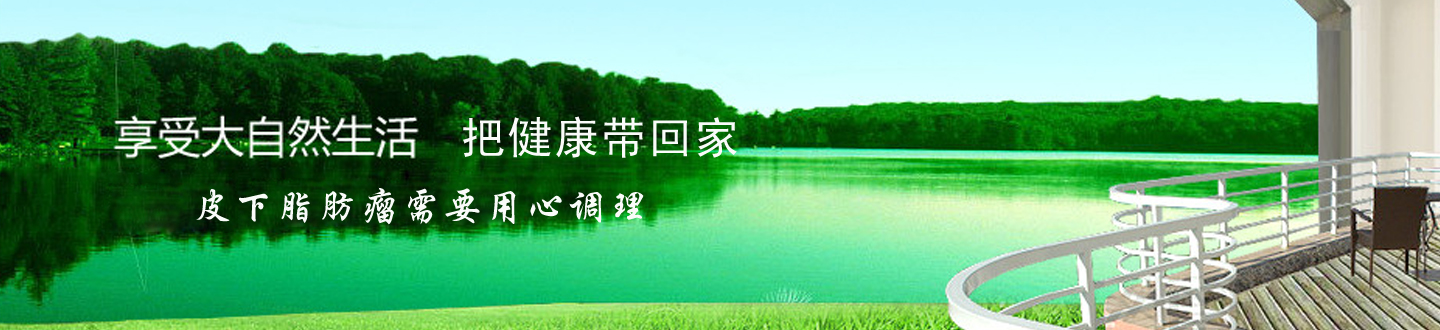
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系首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届国医大师,从医70余年,以治学严谨、经验丰富而著称。临证善于将辨证与辨病有机结合,遣方用药丝丝入扣,治疗疑难病疗效卓著。笔者有幸拜师学习,随师临床,聆听教诲,受益匪浅。现将朱老治疗疑难病的思路整理如下。
朱老认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所谓疑难病是指目前医者在临床上感到棘手的疾病,问题在于“辨证”之“疑”,“论治”之“难”。要掌握“辨疑不惑,治难不乱”,关键是我们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熟练掌握、临床实践的灵活应用,不断探索总结辨证论治的方法与技巧,找到“证”的本质,自可得心应手,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一、怪病多由痰作祟,顽疾必兼痰和瘀
“痰”是体内的病理产物,多由机体功能失调,气道闭塞,脏腑不和,津液凝聚,水湿停留,气化不利而成痰,痰可随处而窜,无处不到。如痰涎窒塞,气道不清,神明之府为痰困蔽,上不能通,下不能达,则癫、狂等怪病以作。如反复缠绵,癫、狂患者舌质可见紫色或瘀斑,精神症状呈周期性加重,此缘于兼有瘀血之故。因为痰气凝滞,气病及血,气血瘀阻,蒙蔽灵窍,而致精神失常,症状顽固不愈。所以朱老在治疗神经精神疾患时,主要是抓住“痰”“瘀”两端,以涤痰化瘀作为神经精神疾患的重要治则,灵活化裁,往往取得明显疗效。
朱老认为“痰”除有形之外,多为无形,其具有明显的特征,主要表现为:(1)眼神呆滞,面色晦暗,或眼眶周围青暗;(2)形体丰腴,手足作胀;(3)皮肤油垢异常,或面色光亮如涂油,其两颊色红者,多为痰火,面呈灰滞,恒为痰湿;(4)神志恍惚或抑郁,或烦躁不宁;(5)舌体胖大,苔白腻如积粉,或灰腻而厚,脉沉或弦或滑或濡缓;(6)易惊悸,烦懊不眠,或昏厥、抽搐,或神志失常。这些痰病的特征显然是与神经精神疾患的症状密切相关。以上辨痰要点,不必悉具,只要见其一二,即可参用治痰之法。对于痰饮的治法,朱老汲取了前人有益的经验,如蒋宝素《问斋医案》指出:“痰本津液精血之所化,必使血液各守其乡,方为治痰大法,若但攻痰,旋攻旋化,势必攻尽血液脂膏而后已。”提出了“治痰要治血,血活则痰化”的原则,达到了“将化未化之痰”行之归正、“已化之痰”攻而去之的目的。
朱老曾多次采用王清任之癫狂梦醒汤化裁治疗周期性精神疾患,该方在化痰活血之中,兼寓养心安神之功,方中桃仁、红花、木通、赤芍活血化瘀,通络宣窍;柴胡、青皮、香附、远志疏肝理气,通络开郁;丹参、酸枣仁养血安神,滋阴降火;佐磁石宁心安神,又可防柴胡之升举太过;茯苓健脾化痰,宁心安神。全方相辅相成,则痰化瘀散而神安。经临床实践证实,每日1剂,连服1个月后,病情好转;再服1个月,周期性发作即可控制。
二、久病多虚,久病多瘀,久痛入络,久必及肾
朱老经过几十年的临床探索,在应用中医药诊治慢性病方面独树一帜。如痹证的治疗,若只从关节肿痛这一标象着眼,而片面采用祛风、散寒、燥湿之法,殊欠理想之效果,尤其对顽痹疗效更差。如患者阳气虚弱,致使病邪乘虚袭踞经络,气血为邪所阻,阻滞经脉,留滞于内,深入骨骱,胶着不去,痰瘀交阻,凝滞不通,邪正混淆,如油入面,肿痛反复发作。所以此证既有正虚的一面,又有邪实的一面,且其病变在骨,骨为肾所主,故朱老创立益肾壮督之法,认为这是治本之道,对根治本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朱老在治疗多种慢性疑难病的过程中,认识到虽然在辨证论治上涉及多个脏腑,但患者每多出现肾阳虚衰之证,经采用培补肾阳法,创制验方培补肾阳汤(淫羊藿15g、仙茅10g、枸杞10g、紫河车10g、炙甘草5g)治疗,均屡验不爽。
林某,男,1岁,年3月11日初诊。
家长诉:腹泻1个月,大便日行5~6次,质稀如水样,经西医门诊与住院治疗罔效。近日症状加重,伴精神萎靡不振,肢末不温,囟门下陷明显。查:大便可见脂质(++)、白细胞(++)。遂来中医门诊求治。
中医诊断:腹泻,证属脾肾阳虚。
治法:培补肾阳,健脾止泻。
处方:培补肾阳汤加补骨脂、益智仁、鹿角霜、炒白术各10g。2剂,2日1剂,水煎服,每日分4~5次温服。
二诊:服药后,即告之患儿腹泻已止,大便每日2次,质成形。守上方继服4剂后,患儿精神转佳,眼睛有神,囟门下陷已有改善,复查大便常规均正常,病告愈。
三、上下不一主从下,表里不一主从里
疑难病病情千变万化,错综复杂,既有上下不一的表现,又有表里不一的表现。在辨证过程中,除了要注意抓住主要矛盾外,还要注意辨明真伪,只有这样,才能在证候分析发生矛盾时,辨证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从而明确治疗。
如慢性肾炎肾病期患者,往往既有畏寒、神疲、腰酸、两腿酸软、纳呆等阳虚气弱的一面,又有头眩而涨、面赤口干、烦躁等阴虚阳亢的一面。在这种“上下不一”的情况下,治疗上既要突出中心,又不能顾此失彼,其重点当以温肾扶阳治“下”为主,佐以育阴潜阳而获效。
又如某女性患者,以头眩而涨,口渴欲冷饮,烘热烦躁,需裸卧冷地得爽为主诉,一派阳亢燥热之象,中西医迭治无效。细察舌苔,色白微黄而腻,边有白涎两条,诊其脉弦滑。乃痰浊内阻之证。合而观之,证属肝阳夹痰,当以清热化痰治“里”为主,乃予黄连温胆汤治之,效如桴鼓。
四、中药剂量恰到好处
前人曾说“中医不传之秘在于用量”,确实是经验之谈。在临床上,朱老强调即使辨证用方无误,但如果处方中药味的用量不恰当(太轻或太重或配合失当),必然会影响疗效。可是这个量的衡定是否恰到好处,与医生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如就益母草而言,不同疾病中用量不同。在治疗高血压时,朱老指出:“益母草有显著的清肝降逆的作用,对产后高血压尤验,但用量必须增至60g,药效始宏。”他曾创制“益母降压汤”,处方由益母草60g、杜仲12g、桑寄生20g、甘草5g组成,伴头痛甚者,加夏枯草12g、钩藤20g、生白芍12g、生牡蛎30g;阴虚甚者,加女贞子12g、石斛15g、生地黄15g。在治疗肝硬化腹水,症见腹大如鼓、腹壁青筋显露之鼓胀时,恒以益母草g(煎汤代水)加入辨证方药中,常可减缓胀势,消退腹水,因此证乃气血水相因为患,恒多“瘀积化水”之候,而益母草具有活血、利水之双重作用。
另外,朱老常用豨莶草g,配合当归30g,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效果很好。随着风湿活动迅速控制,抗“O”每见下降。又如用细辛治疗痹证疼痛,无论风湿、风热均可用之,但是寒证用量宜大(10~20g)、热证用量宜轻(3~5g)。
曾治一“结节病”患者,以周身出现皮下结节、不痛不痒、推之能移、逐渐增多至80多枚已1年有余为主诉,伴胁痛脘痞等症。病由气结痰凝所致,治宜活血散瘀、软坚消核。处方:生半夏7g,白芥子10g,制海藻、昆布、夏枯草、茺蔚子、紫背天葵、炙僵蚕各12g,生牡蛎30g(先煎),川芍5g,红枣5枚。患者服10剂后未见动静。二诊时守上方生半夏改为15g。服10剂后痰核逐渐减少,至30余剂后痰核基本消失,转予益气养阴、软坚消核之品善后。朱老认为,凡顽固性痰核,非生半夏不为功,生半夏的用量对疗效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而证明对药量的把握也是提高治疗疑难病疗效的途径之一。
五、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中医以辨证论治为核心,但并非不辨病。朱老结合西医的辨病,创制了临床行之有效的经验方。如治疗慢性痢疾及结肠炎的“仙桔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益肾蠲痹丸”、治疗痛风的“痛风冲剂”、治疗慢性胃炎及消化道溃疡的“胃安散”、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及早期肝硬化的“复肝胶囊”、治疗前列腺肥大的“温肾利尿方”等,均屡建殊效。
朱老所创新方,组方缜密,遣药灵巧,寓意深远。如益气消癥汤是治疗慢性前列腺增生的经验方,由黄芪30~45g、莪术10~15g、鳖甲15g、皂角刺12g、益母草20g、土鳖虫10g、泽兰15g、苦参15g组成。治此朱老始终抓住肾气不足、气虚瘀阻这一关键病机。采用黄芪与莪术相配以益气活血、化瘀生新,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指出:“参、芪能补气,得三棱、莪术以流通之,则补而不滞,而元气愈旺。元气既旺,愈能鼓舞三棱、莪术之力以消癥瘕,此其所以效也。”配合益母草和营祛瘀。土鳖虫化瘀通淋,因其性味咸寒,入心、肝、脾三经,是一味最平和的活血化瘀药,凡血瘀经闭、癥瘕积聚、跌打损伤、瘀血凝痛用之均有良效,其特点是破而不峻,《长沙药解》说它“善化瘀血,最补损伤”。鳖甲、皂角刺软坚散结。泽兰行下焦气滞,芳香以开膀胱之气闭。苦参泻化瘀浊,以清下焦湿热。全方合用共奏“消坚祛积,扶正祛邪”之并驾齐驱的作用。因此在临床上应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抓住该方益气补虚、活血消癥的治法特点,根据异病同治的理论,运用益气消癥汤治疗因阴阳俱损,肾气亏虚,气化不行,瘀阻逗留,呈现本虚标实之证,如闭经、子宫肌瘤等疑难病疗效卓著。
综上,朱老论治临床疑难病思路开阔,层次分明,注重在经典理论指导下,理法方药一脉相承,疗效卓著。
版权声明
shengming
本文选自《万文蓉临证心悟》(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万文蓉著),最终解释权归原作者所有。由中医出版(最好白癜风医院咨询北京治白癜风要花多少钱
转载请注明:http://www.nwoab.com/zysx/1775.html